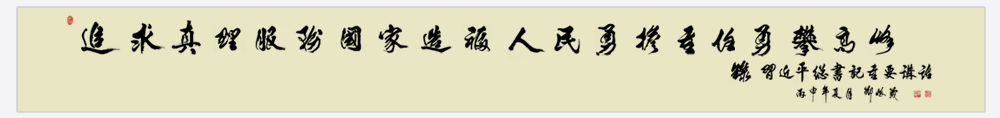
摄影的心理获益
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
在精神分析学与东方哲学的交汇处,"镜像"这一隐喻始终是人类认知自我的核心命题。著名心理学家、哲学家拉康在《穿越“我思”的幻象》中提出:人究其一生,都在寻找真实的自我。而寻找验证自我的主要方式,是通过把他人作为镜子,与他人互动中根据对方的反馈,获得镜像,也就是建立了自我认识,人类必须在社会镜廊中寻找自我存在的坐标。这也与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中所说: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,有相似之处。
因此,人作为社会群居性动物,必然要不断与他人发生联系和交互,这也是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的重要条件。如《周易·同人卦》:“同人于野,亨,利涉大川,利君子贞。”很多相关研究和我们的临床经验已经证实,如果长期处于封闭、闭塞的环境,与人交流减少,会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发育,产生人格障碍、行为障碍,焦虑抑郁等;而对于老年人来说,则会明显增加罹患痴呆的风险。
对于一些患有严重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患者,由于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的受损,以及自卑、自我评价的下降等因素,逐渐远离社会环境和人群,进入了较为封闭的个人环境中,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精神心理问题。在脱离社交和正常社会活动后,由于缺乏他人反馈,从而对自我评价和认知的镜像,被主观的幻象和推测所取代,加重了自我的悲观绝望、无价值感、空虚感、无归属感、无安全感等负面情感,最终使得焦虑抑郁、偏执等情绪不断积累,一方面对个人精神产生反刍式的折磨,即不断地反复思考对个人的负面评价,极大地增加了精神痛苦;另一方面,精神痛苦、焦虑抑郁让患者本就敏感的神经更加活跃易激惹,从而对躯体病痛的感受更加敏感和扩大,使得躯体痛苦放大和加倍。因此,他们的认知图景经历了双重坍缩:外部镜像的缺失催生内部认知偏差,而扭曲的自我叙事又加剧社会疏离,最终形成病理性的莫比乌斯环。
对于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,并且远离社会环境和人群的患者,如何继续维持或者加强与社会群体的沟通和交流,对于提升自我认知,缓解精神和躯体痛苦,改善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,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摄影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,摄影后再通过患者本人或亲友的平台发布,是维持社会活动的另一个选项。这种创造性互动本质上是对拉康"大他者"理论的当代回应,印证了海德格尔"在世存在"(Being-in-the-world)的哲学洞见——手持相机的过程,即是重建主体间性的存在论实践。
自我拍摄中,不仅仅是从摄影中观察获得自我的镜像和评价,增强自我认知。还可以为无法清晰表达情感的人(重度抑郁或语言障碍)提供视觉化出口,传递内心状态,提供社交机会,减少孤独感,促进社会理解;帮助建立生活节奏和改善动力缺失,建立与他人沟通的桥梁。通过系列照片讲述个人故事(如康复历程),帮助整合创伤经历,赋予生命新的意义,完成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愈过程。正如敦煌壁画中"镜中佛"的隐喻,当拍摄者在镜头前后凝视自我,他们正在完成从"被建构的主体"到"自觉的创作者"的存在论飞跃。同时,完成摄影作品可带来掌控感和成就感,尤其对因疾病感到无力的患者而言意义重大。
另一方面,由亲友或专业摄影师拍摄,除了以上的获益,还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和丰富的形式,比如将摄影与写作结合(如为照片配文),或与音乐、绘画联动,形成多感官疗愈体验。并且专业人士更能够帮助发现生活中的积极元素,把握美或者意义的瞬间(光线、色调、生活细节等),更有助于打破“负面认知偏差”,提升积极体验和自我价值。如专业摄影师、艺术家发起的“残障美学”项目,对残障人士进行拍摄,重新定义身体形象,挑战社会刻板印象,增强了残障人士的自信。“100个抑郁症女生的写真”项目,通过视觉叙事引发社会共鸣,强化参与者的社会归属感。多项研究表明,摄影疗法可以降低参与者的抑郁、焦虑量表分数,从而报告更高的社会归属感。
因此,通过摄影行为,自拍或者专业拍摄,使得参与者能够建立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提升自我认知和价值感,有叙事疗愈的心理治疗价值,在力所能及和允许的情况下,进行摄影相关的活动,从而获得内心的和谐:与人和谐,与物和谐,与事和谐,最重要的是与自我和谐。
摄影不仅是记录工具,更是一面动态的“社会之镜”。它让患者在凝视与被凝视中重构自我叙事,将孤立的内在世界转化为可共享的视觉语言。正如存在主义治疗强调“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”,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,患者不仅在捕捉光影,更在主动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。这种创造性的联结,或许正是通向“与自我、他人、世界和解”的隐秘路径。
供稿: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